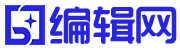编辑网讯 www.bianji.com 你见过六七十年代的衣服么,那时候的衣服非常粗糙,在现在的我们看来,那样的衣服可以被称之为帆布了,帆布鞋的帆布。和纤维纺织业发达的今天生产出来的衣服相比,七八十年代的衣服可真不是那么的有个性。
那天我洗衣服,有一个非常好的针织毛衣,当洗出了后才发现甩干机坏了,我就拧了拧挂了起来,针织毛衣开始往下坠,我顿时觉得,这个毛衣还真是娇贵,像这个时代的人一样。假如是七八十年代的那种衣服,大概不会轻易的变形吧,可以洗很多次,穿很长时间。
而现在,羽绒服需要送到干洗店,蝉丝围巾也要特殊清理,各种衣服都不一样,在彰显着它们的个性。在七八十年代,个性是珍贵的,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,个性越来越显得唐突,没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唯一的不一样的,于是觉得平凡难得可贵的人成为了另一种个性。
并不是说个性是错误的,这只是时代发展的产物,但我始终觉得,当时复杂的事物在未来会变得简单,觉得曾经简单的事物在未来也会觉得复杂。这就像宏观上的历史一样,天下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,简单的事物会变得复杂,复杂的年代里人们会追求简单。
七八十年代的衬衫适合七八十年代人们粗糙的皮肤,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人们也可以穿,你可能觉得它们俗气,但是它们并不是那么的娇贵。
生命是彩色的,红色的是痔疮,黄色的是糖尿病,蓝色的是腰间盘突出,绿色的是近视,白色的是脱发,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他自己的颜色。就像那首歌唱的那样,“我就是我,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”
生命短暂的像烟火一样,命运给我们的身体添加不一样的颜色,这是人生最直观的颜色,你能否将自己灵魂深处上色,谁又会去探索你灵魂深处的颜色。
人生啊,其实最大的磨难是如何让灵魂更好的适应身体,不要等到失去了意识才幡然悔悟,人生原来这么短暂,我却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修改“身体的颜色”上,虽然我曾爱过一些人,但却不曾过多的爱过自己,我“灵魂的颜色”是如此的空虚。
人生努力的去将自己灵魂的颜色涂成一种绚烂的色彩,去专注做一件事,去追求一个事物,我想,是非常有成就感的。纵使人生繁琐,时常感到疲惫,但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,即便是身体的颜色也是可以忽略的。
我曾经被一行字所感动,“我们人生,没有两全”,不是那么多的事都能顺从我们的心意,想要抓住一件事物,就要放手另一件事物,它从侧面也在说,其实,我们人生应该去追求独一的事物。
生命是彩色的,身体从没有放弃它的颜色,正是因为身体有着颜色,我们才能看到生命的存在,才能看到生命的逝去,才能看到生命的残忍与美好。
但我知道,灵魂是可以有颜色的,王小波像一轮红日般的颜色,杀遍了人间的噱头;冯唐还是黄灿灿的尿骚味,谄媚的说自己是庸俗中的贵族;史铁生遁入深蓝色,是《我与地坛》封面的颜色,让人觉得人的灵魂是平等的;贾平凹以棕木色在说愿人生从容,柴火上是一锅汤,越煮越有味,你要怎么去明白“熬”的人生哲学。
我们人间,有两种人,有两种声音,不鸣宁死的人不轻易说话,哗众取宠的人不说轻易的话。
不鸣宁死的人非常少有,但也不在少数,有些人不明白,生命是如此的珍贵,为什么还要不惜去死还要说一些话。这些不鸣宁死的人其实是想做自己,当灵魂真正贴合了身体,会发现这个世界对少数人是不公的,所以即便死亡,我也要证实自己的存在。
唯有存在才会被记忆,唯有记忆才证明存在。
时代不曾记忆住所有人,大多数人奠基了时代,但时代却抛弃了大多数人,我们不曾在被遗忘中逃走,但一些人可以证实自我的存在。证实自我的存在,首先是向自我证明,就像儒学之人想要拯救世界首先要做的是正心诚意,往往做不到不鸣宁死之人都在于做不到正心诚意。
生,人生,生命,是有声音的,生之响往,生命的声音会去向何处,假如身体与灵魂到达不到的地方,那就用声音传递自我存在的意念吧。
不鸣宁死往往会陷入“虔诚的困境”,为了鸣而死。其实之所以“鸣”就是为了更好的生,向自我证明自我的存在,向世界证明我是不可以被忽略不可以被打压的。
当不鸣宁死失去了理智,总是用感情来呼救,他们不再证明“自我的存在”,他们证明的是“证明自我的存在的虔诚之心”,不鸣宁死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,这种形式主义以生命作为威胁让他人产生一种内疚,这种“不鸣宁死”变成了“哗众取宠”。